人物介绍
彭茂,2015级人文学部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友,本科毕业时从文华考上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的研究生,毕业后考入东北师大附中深圳学校,担任高中语文老师。在文华学院时,曾获得国家奖学金,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湖北省外语翻译大赛一等奖、优秀毕业生等荣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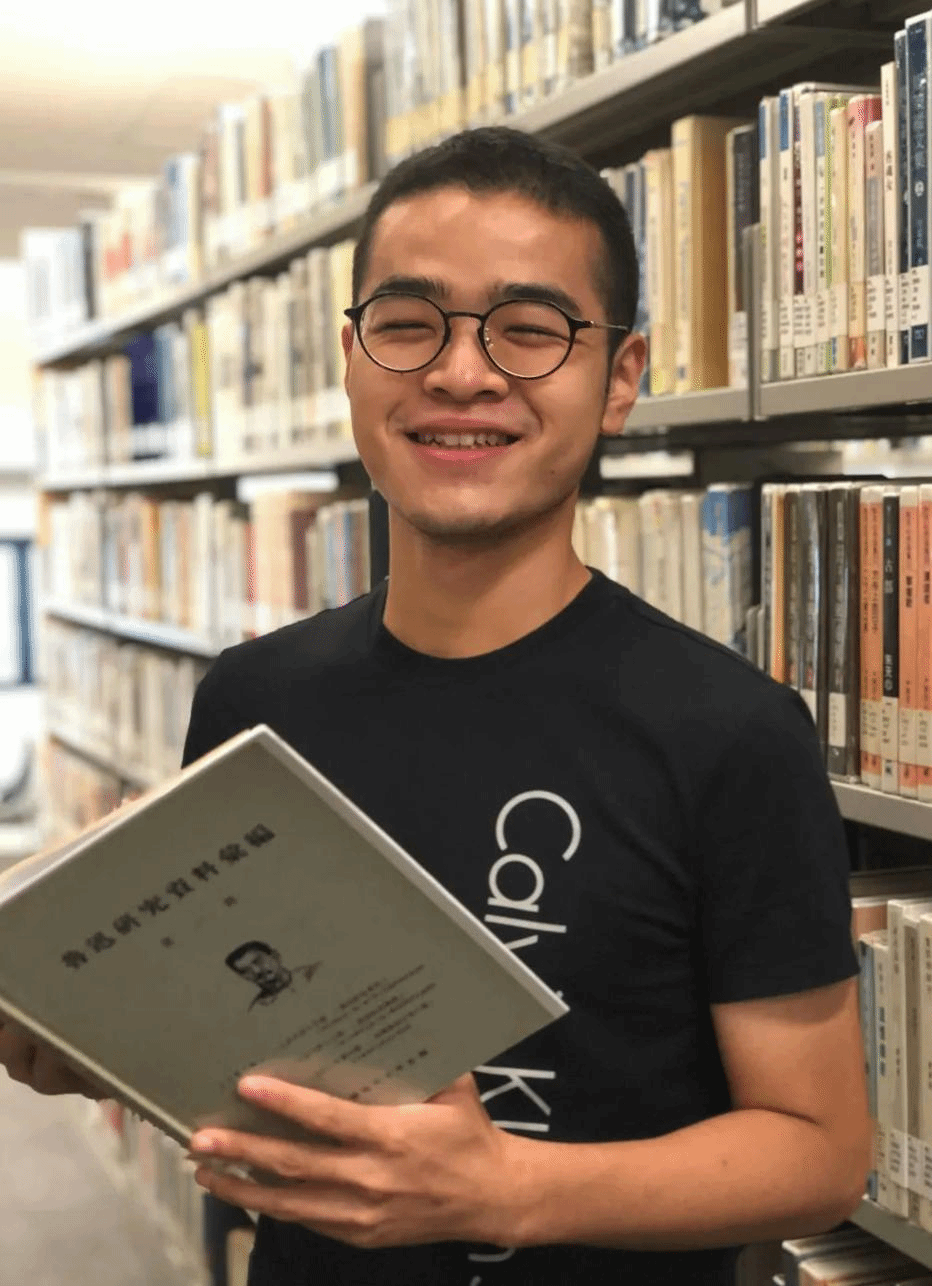
逝去的岁月如鲁迅所说,是“坟”,钩沉往事“一面是埋葬,一面是怀念”,是饱含怀旧意味的回首一瞥,亦是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不会过去。类似考古学究似对逝去人生的考量与审视,不放过“过去”,竭力打捞生命陈迹的吉光片羽,颇有“仪式感”刻意地回到自我生命生长的历史现场,回到生命发生的原点,更欲求那些曾习焉不察的隐秘角落。“过去”是死去的“坟”,在我看来,亦是潜在孕育未来生命路径的“巢”。我想,这便是我追忆过往且将其见诸文字的意义。
步履不停的匆忙,或是一些潜在伤痛不可名状的无意识回避,好长一段时间来我拒绝直面它,全然没有拥抱往事的勇气与提笔记述它的力量。但我也知道,若永远沉湎于“往事不堪回首”的逃避,过去的缺席便会像黑洞一般时时让我陷入“我是谁”的追问泥淖中。那就借着校刊约稿的契机,停下脚步,悬置感伤,不妨回头看看这过往的路,看看那些或彰或隐,特别是那些隐而不彰的幽微处。写下这些絮语,为着感恩给予人生起点的母校文华,为着致敬给予我鼓励及帮助的师友,为着感怀一直守望相助的伴侣,为着自我救赎,也为着这一段认真过活的人生段落与时时未放弃的自己。
求学:我的文华底色
高考自己考,学校自己报,专业自己选。和大家一样,我也是因为高考失误或志愿填错等诸多其他原因,来了文华。但不管怎样,自己选择,自己承担。调侃归调侃,回望文华的日子,恰是在文华中文的四年,给了我追寻文学的勇气与底色。
怀抱对中文系与大学生活的诗意想象走进文华,但真实境况却令人烦闷、鄙夷,甚至一度想出离。枯燥的专业基础课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应用文写作全然没了文学的诗美,不禁犹疑:我真的喜欢中文系吗?繁杂的学生工作与名实不符的活动令人失望疲沓,不禁再度犹疑:我真的有组织管理的领导力吗?无助与失落,一度使我动了复读的念头,从头来过,重新选择。渐焦躁而时自责,多苦闷而孤僻,心中呐喊:我的青春怎就一塌糊涂?
转机在入学三个月后,2015年11月。人文学部举办了一系列的将毕业的优秀学子分享本是为了凑人头充数应付,不曾想从中发现了“微光”。榜样们耀眼的经历与履历令我兴奋。原来文华的学生也可以很优秀。但激动之后便想要追问:该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大一生活又是怎样度过?一个又一个的疑问想要解答。会后我私下约到了这些前辈们,向他们讨教,在一对一的交流中,我聆听到更真实的人生体验,面对逆境,他们也曾苦闷彷徨......有中文系的邹慧嫚学姐、朱清学姐、新闻系的毛传俊学长......是他们告诉我,要扎实认真学习专业课,这是“本”,要勇敢尝试学生工作,哪怕不成功......那时候,这些比聚光灯下更为真实讲述给了我莫大的勇气与力量:我也要像他们一样——“优秀”(成为他人眼中最闪耀的仔)我试着从上好每一门专业课开始,试着积极参与班内系部的活动,一时间苦闷彷徨暂缓,虽然依旧迷茫,却很充实。大一结束时,在广泛的尝试中,我才渐渐悟出:尝试并不一定都要成功,不成功的尝试不一定没有意义,意义恰在于可以不必在不适合的道路上死磕;“优秀”不一定是面面闪耀,“优秀”不一定需要他人看到,做好自己喜欢的事情便可。

彼时,我重心转移到学习上来。初高中的语文课堂为我种下对文学的向往,初入大学却因课程枯燥而质疑“爱好”本身,沉潜一番过后,又再次深深神往。这是“恍然大悟”,亦是“后见之明”:爱好兴趣是个伪命题。在山门之外仰望峰峦翠微顿时心旷神怡,心生欢喜便欲跋之涉之;行至道上却因道阻且长心生胆怯便欲退之逃之;而当硬着头皮、遍历这途中的艰险,极顶登峰,便又会心生“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之盎然。所以,凭着最初对“语文”的喜爱,扎实地学习“枯燥无用”的中文系课程,苦乐中回首向来,追寻文学的道路宛如“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是为“风景”。
而我可敬可亲的老师们恰是这曼妙“风景”的展卷人。从小到大的语文老师罗芷玲、何哲钰、谢娟老师给了我最美妙原初的文学初体验。进入大学,在专业学习上,文华中文的老师们都耐心地为我解答每一个问题,在问答中我探寻到文学与文化的深沉、深刻、深邃;在发展方向上,谭邦和教授、廖超慧教授、孙斐娟老师、卢云芳老师、方蔚老师、刘晶老师、彭晓艳老师、肖金云老师等多次鼓励我:“彭茂,你应该去更好的平台,你值得去更大的舞台”,这些许“夸张”的鼓励中饱含着老师们对我的信任与热望,辅导员胡晓勖老师、顾念念老师也在学习和生活上给我以全力支持。那时稚嫩的我,相信便笃定,有力而自信。
四年中,我跑遍武汉地区高校,但凡是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关的讲座论坛活动,我无一不热望前往,风雨无阻。仍记得在华科“春秋论坛”上,贾平凹《文学与地理》、迟子建《读书的年华》、余华《阅读与写作》这些活跃于当代文坛中的著名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分享,也还对谢冕、罗振亚、姜涛在武汉大学“文华讲坛”所做的《中国新诗历史现状与未来三人谈》讲座记忆犹新。2018年末我通过申请,获得了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在京举办以“文艺评论家眼中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为主题的评论年会唯一本科生的参会资格,聆听仲呈祥、王一川、程光炜等七位专家学者从文艺政策、文艺理论、当代文学等不同视角讲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文艺事业的曲折发展、不断创新和辉煌成就。通过参加文学学术活动,理论意识逐渐培养起来:从对作品感性地鉴赏认知,到对作家生平,创作背景,作品生成以及文学机制构成的深入探索,发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复杂与深邃,更坚定了我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兴趣方向。渐渐发现文学不仅仅只是文学,它是我们认识复杂社会时代的一个窗口与途径,透过文学能抵达更深邃的世界。而中国现当代文学较于其他文学研究领域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当下介入性,以及它的复杂深刻之处能反映中国近现代化的历程,更隐喻了当下之所以为当下的奥秘。那时便下定决心:去更广阔的天地,探寻文学、时代与我。
四年扎实的专业课学习,全系排名第一。带给我不仅是国奖等荣誉,更是继续文学深造的资本与对文学研究纯粹热爱的笃定。毕业临近,我被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录取,在全国研究生考试中也以笔试第二综合第一的成绩被广州某校现当代文学专业录取。最后,我选择负笈香港,在更别样的天地中去“探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
读研:“突围”汉口,“漫游”香港
一样是摩登繁华,一样是鼎沸喧嚣,一样是人来人往、步履不停。旺角东日夜嘀嗒不息的红绿灯下接踵着各色不知来路亦不明归处的匆匆赶路人,目及暴雨后氤氲中恍惚的车水马龙,醉眼迷离竟不知此时此地是“汉口”抑或“他城”香港。二十三岁第一次出门远行,窃喜在困囿汉口的十二个年头,终可突围这烦闷的江城和已熟悉到厌倦的家。天真地以“寻求别样”来标榜远行,幻想中所抵之处皆是新奇、美妙、五光十色。
言语不畅,饮食不合。抬眼望及闪烁着的港式霓虹灯,迷惘在这热闹却也冷清的他乡街头。逼仄小房间里冷气机的噪音与窗外疾驰飞车所留下的鸣笛相交错,繁华精彩与我无关的此地,是想象的“别样之境”吗?离开故乡时的激动与期待早已骤降至冰点,由爱至厌似乎只在一瞬间。我开始怀念我逃离的汉口。于“他乡的此处”遥忆“他方的故乡”,忘却了叛逃时的决绝,汉口曾被我烦闷的一切在滤镜式的追忆中染上浓浓乡愁。我捧读着池莉、方方笔下“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汉味烟火聊以自慰,那粗粝暴躁的汉骂多么亲切、那街头巷尾摇着蒲扇纳凉的人如此可亲...... 渐次在时空睽违的隔中生出“我本是江南的人来江北作客,不忍想家乡此时寒雨正纷纷”的失意零落之愁。
我好摄影。人潮汹涌的街头、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下,香港的多元图景时时吸引着我用帧帧光影记录下此地的绚烂风流。也许,我之于香港仅仅是“在而不属于”。可正因如此,总是以因求学寓居此地的过客心态来将“我”与“他们/他乡”区隔开来,躲到对故乡无限的思念沉湎中。

而在学研方面亦曾经历炼狱般挣扎。紧凑的研讨课程、每周近百页的阅读材料与千字读书报告,另一面还要兼顾导师选择和论文选题,凡此种种早令人疲沓心累,好在那时有至爱的鼓励打气,“硬着头皮往前走吧”,这话像神谕般,关关难过关关皆过。在导师选择时,“出身”像隐悬于我头顶的暗箭一般又再次显现,但这一次我并未“自卑”,我深知自己本科鲁迅研究的毕业论文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加之在香港的几门跨学科课程中也已习得了较新颖的文学文化研究视角,所以在给导师千字自荐信中自信而虔诚地介绍了自己与论题思考。没想到老师十分肯定我的鲁研视野与文学基础,就这样我成为了东亚汉学章鲁研究学者林少阳教授的学生。林老师此前在东京大学任教,在指导我论文时,总告诫我要跳出二元对立的视野与绝对化的价值叙述去爬梳史料,去触摸相对真实的历史,以此才能接近一个“真实的鲁迅”。当我苦恼于鲁迅研究作为一门显学,向导师表示“小白的我”想要独辟蹊径实在难于上青天之时,导师严肃地说:你有真正反思前人研究的成果吗?核心期刊的名家文章一定都是精品吗?为什么不去看看港台和海外的鲁研成果?你来香港继续鲁迅研究的意义是什么……直击要害的问题让我羞恼,却又令人深省不已。痛定思痛,当沉潜到更广博的历史文化视域与史料中时,研究思路渐次清晰,论文最终得以顺利通过答辩。回望在香港的求学时光,所修课程几乎全获A,并以全系前5%的Distinction degree毕业,几经波折的硕士论文《从“鼎革以文”到“立人以文”:再探近代中国语境下章太炎与鲁迅对文学义界的开拓》亦入选《文史刍论》(2021年11月香港出版),但更内在的获得是何以为“学术”,何以为“批判性思维”,且时时警惕自己的“狭隘”。
当社会动荡与全球疫情侵袭着香港时,众多同学离开香港。当时说不清为什么,我选择留了下来。每日五点晨起,于沙田河畔长跑一小时。晨光熹微,亦有习习凉风送来沙田马场的青草马粪夹杂之异香,早已面熟的跑友插身而过时还会为你竖起大拇指说“猴fai啊猴赛雷”,不由感叹:这是我想要的生活。跑罢回家做一顿元气早餐补充能量,接着便乘8分钟的港铁抵校,“藏”入阒无一人的地下四库全书阅览室,开始一天的论文事宜。周末会在和好友行山探海,游荡山海间,一周的辛劳可在自然中挥散全无。以往众人对香港的认知不过是购物天堂或是钢筋怪都,对于香港人的看法也不过是冷漠加黑脸,但当我真实在此地生活时,刻板印象轰然崩塌,我眼看香港:是山林城市,亦是温情之都。

那刻,我想要在香港生活下来。课余做了多种尝试:曾任大学预科中国文学导师,教授IBDP中文A课程,指导国际学生运用文学理论及文本细读的方法撰写文学评论文章。任香港副学士中文科讲师,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帮助文学基础薄弱的副学士入门文学文本的细读分析以及文学学术论文写作;任香港恒生大学大湾区融创中心(HK)文案编辑实习生,负责设计恒生大学期刊、选稿汇编以及日常文案撰写工作。但最后因为一次在疫情正严重之时的突发高烧,改变了我继续漫游香港的想法。核酸检测未出结果之前,忧虑而恐惧,我不敢告诉任何一个人,焦灼等待中,独自躺在床上的我,突然想家。所幸是一次普通感冒,痊愈后旋即便收拾行囊,回家。
回眸汉口,一瞥港城。似乎真如昆德拉所说:“真正的生活应当永远在别处”。奔向他乡别处的意义也许正在于不断重新回望过往,亦不断去忘却经验而纵情体验新的生活,在模糊了新与旧、故土与他城的边界中去“道路以目”。回首且长长的一瞥,“他城”、“我城”皆是新景,“他们”、“我们”亦是景中人。感恩漫游港城的旅程,别样亦精彩!
未来何处?惶惶不可知。蜉蝣寄世,也许依旧不过是从他乡奔向他乡的逆旅。
求职:将追寻“别样”进行到底
回到内地,亦面临求职的选择。成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能继续我对文学的热爱,选择深圳,却是因为它以“双区”的独特优势令我向往,就这样我加入到深圳教招求职的泱泱大军。从隔离解封便奔向全国各地的深圳教招点,短短一个月间,北至哈尔滨、北京,南达广州、深圳,东至杭州等地,参加的笔面试累计二十多场,可悲的是无一offer可获。
此刻的我,似还未上场亮剑的将军,意气全失。回到内地,未在家中休憩,便跑了大半个中国,疲惫、孤独、只想嚎啕大哭,我不要这样狼狈回家。记得在哈尔滨,参加完面试知晓自己没能进下一轮,愤从招点冲出门,奔向马路,谁曾想下午四点半的北方早已漆黑一片,四下里是被雪覆盖的白茫茫一片,也不知是何处来的一股劲,寒风吹彻着,我顶着漫天大雪,边跑边哭,黑天白地苍茫间,无人知会,跑累了便席地坐下,看那白雪铺就的道路延展到消失在视野,听那朔朔北风狂啸在耳际,四下寂静无声,热着跳着的还有也只有我这颗千疮百孔的心。不屈的心似乎又回来了,捧着这心,面对这恶火,害怕却不退缩,我告诉我自己:我要走下去。
痛定思痛,反思自己的确在教育教学知识以及授课经验方面还有很大欠缺,又恰逢深圳一些高中招聘顶岗教师,我连夜赶到深圳参与现场面试,历经二十多次“失败”的我早已沉稳不惊,面对老师们的任何提问我自信地娓娓道来,遇到不会的问题也诚实应对并告诉自己思考问题的角度,当然“出身”问题毫无疑问成为了最后一关,我微微一笑,说到:纵使本科未能带给我名校光环,但在本科四年我已经竭尽所能做到了最好,我认为一本二本三本学校间的差异更多的是平台资源的区别(当然有待商榷哈),而不会命定我们为一类二类三类的学生,我认为我还不错(羞涩脸)。我走上文学的道路全然是因为语文课堂,让我在青春懵懂且孤独的年纪有一个与自己对话的精神自留地,我感恩语文,感恩文学,我也希望能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像我的语文老师一样帮助像我一样曾迷惘的学生。如果说“出身”是这个社会的门槛,那我愿意继续等待跨越门槛的时机,但还是希望老师们给予我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这是我历经二十多场面试唯一通过的一次,虽然不是编制内的offer,但它至少暂时能让我在深圳教学一线学习,亦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鼓励:“出身”并非禁锢人的铁律,只要我足够努力。
一面担任两个高一班级的语文教学,也一面反思总结自己的“失败”面试史。

机会确实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年关将至,深圳教师只能留深过年,深圳对我来说其实比香港更陌生,举市欢庆,举目无亲。寒假便一人在空荡的办公室备课读书,练习更标准的普通话(湖北口音太重),独酌孤独。
此时2020年秋招早已落下帷幕,我静待着来年春招的到来。也许是上天眷顾,看我这一路太苦太难,除夕前十天我收到了东北师大附中深圳学校初审通过的信息。激动而惶惑,兴奋罢又渐次冷静下来。连续十天的笔面试,令人紧张疲惫而又惊心动魄:高考题测考笔试、高考题评析笔试、高考出题笔试、一轮面谈、试讲、最后走到终面。其实在每一轮中都位居靠后的位置,我却没有丝毫气馁,相反这次自信爆棚,在千余人名校生的角逐中,二本学生走到了最后。老师向我继续追问“鲁迅”:学者汪晖的鲁迅研究代表作是什么?我答:(内心窃喜)是八九十年代的《无地彷徨》,一顿猛说,结合小说及散文诗解释其“历史中间物”思想,老师直打哈哈说可以了。老师又问李长之研究鲁迅的专著是什么?我答:(内心再狂喜)《鲁迅批判》是最早的系统地研究鲁迅的专著,讲到书中框架和其在鲁迅研究史的特殊意义时,老师说可以了。本硕阶段认真踏实研习的“鲁迅”在此刻闪光。
此时,我知道还有那个“无处遁逃”的问题。老师问:民办独立的本科学习会不会是一种局限?
(此处省略五分钟,如前次深圳顶岗教师面试差不多,老师耐心听完。)
直到除夕早上九点,我收到了录取通知,还在被窝的我嚎啕大哭。很巧的是,陪伴我的小爱同学随机播放了极古早的《三百六十五里路》:“睡意朦胧的星辰/阻挡不我了行程/多年飘泊日夜餐风露宿/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
我想,这歌冥冥之中便是为我这走过的路所下的最好注脚。回望来时路,风风雨雨都迷人。我满怀着感恩与感动,感怀毫无条件支持我的家人朋友,给我发展平台的母校与恩师,还有现在虽各奔前程却一直守望相助的伴侣,以及那个从不放弃的的自己。
下一站,我会更坚强,继续寻求别样的人们,追寻别样的人生。